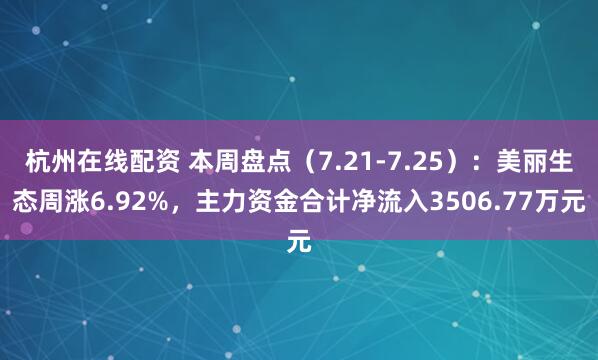清理阶级队伍杭州在线配资
春天之后,渐渐到了运动后期,事儿也还有不少。
首先一个就是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这是社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。就是重新清查各人的阶级成分,有没有错划、漏划的。
在那个年代,每个人都有两个政治标签,一是“本人成分”,是指本人参加革命工作或入党以前的个人社会地位。解放后出生的一般就是“学生”。第二,最主要的是“家庭出身”,是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的家庭阶级成分。
阶级成分应以土改或土改复查和民主改革划定的为准。意思是,比如有个人中学毕业参加工作当了个工人,但他并不一定就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,如果他家里是地主成分,那他就还是地主出身。
图片
图片
图片
1,中央有关划分阶级的文件。2,1965年5月13日,黑龙江省阿城县料甸公社对四类分子的训话会。3,四类分子签下的“改造保证书”。
图片
图片
1,这是文革时期的“阶级成分登记表”。文革的中后期也有个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的工作。2,文革时的《划定家庭出身通知书》。通知书里把四人的家庭出身定为革命“职工”,其实家庭出身里是没有这一项的。
图片
图片
这是已经到了1984年,因为电脑网络运用日渐普遍,为输入的方便和规范,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出台了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的代码,并被国家标准局分别以“GB4762-84”和“GB4765-84”的标准号,列为正式的国家标准。直到2004年才停止使用。图1为“政治面貌”的代码。图2,家庭阶级成分的代码。
在那时的社会体制下,“家庭出身”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政治地位,决定了你是“主人翁”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“罪人”。不但决定你的命运,还决定了你全家、你整个家族的命运。
而且,如果没有特殊情况,家庭出生还是世袭的,即地主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,还是地主,哪怕那块地在他爹的爹的爹的那时就已经被土改分了,哪怕早就流落到千里之外,跟那块地一点边也没沾过,那也不行,一出娘胎那就是小地主。
尽管在不同时期、不同的文件上,对如何划分“家庭出身”有着很多的政策规定,甚至有详细的量化标准,比如剥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百分多少以上算地主,多少到多少算富农。各地各个时期的具体标准不一样,一般是剥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25%以上算地主。
但就算是这样明确,实际上也是很难算准的。比如某人有十亩地,种不过来,请一个人来种三亩(叫佃农),自己种七亩。每亩收二百斤粮,佃农每亩交五十斤粮。那剥削率是按30%(600/(600 1400))算呢,还是按10.3%(50*3/(50*3 1400))算呢?如果不是租出去,而是雇佣一个人来和自己一起种,那这个雇农的劳动量在两个人的劳动总量里究竟占多少,就更算不清了。
图片
图片
图片
图片
1,改革开放后,报纸刊登的党中央对四类分子的摘帽决定。2、3、4,此后各地不同的“摘帽子通知书”。
图片
河南省辉县有位粟明英,她的戴帽通知书和脱帽通知书还都在。
整顿党组织
这也是运动后期的一项重要工作,其主要内容有:对原有党员重新登记,依据其四不清的程度和对运动的态度进行处理。有的开除,有的劝退,有的延缓登记,有的给予党纪处分,并吸收一部分积极分子入党。
这项工作对于我们下去的学生来说,挺别扭,尤其是为发展党员的事。
那时学生党员极少,从入学到那时还没有发展过(还是社教回去以后才有发展的)。自己不是党员,连个团员也不是,反而还要发展别人入党,从筛选对象开始,帮他写入党申请书,帮他填表,教他怎么回答组织的谈话提问,一整套的程序、手续,都要全程帮他做,都能赶上专职组织干事了。
而那时的农村青年还远不如当下的年青人,闭塞得很,很多政治上那怕是很常识的事情,不但不会讲,就是讲给他听还听不明白。他们的积极性好像也不高,既不明白,也没有更多的想法,硬是在给他们办的。
我那时也想过,怎么这入党的标准在城里和在农村还不一样。或许让他们入党,相对来说不怎么会添乱。
在湖南参加社教的一年里,好像很少单独进行党组织活动,那样的话,我们就会很尴尬(老师里面也有不少是非党群众的)。有的话,也是一起参加的。
图片
整党工作的材料
“分配胜利果实”
从程序上说,这跟生产队搞分配相类似:把退赔来的东西加起来,一共值多少钱,再把全队人数(除去四类分子、四不清干部和家属不算)一除,就是每个人能分到多少物品。可是这些东西一共没多少,平均一人也就是相当于三五块钱。
但是具体操作很费事。首先这些东西,很难分。比如某干部要退赔三十元,他又没有钱,那就拿实物来抵。他从家里拿出一张比较好的桌子,经工作组同意后,就折合成三十元。
但分的时候就麻烦了,如果每人能分五元钱的“胜利果实”,这桌子就得分给六个人,得两家、甚至三家凑起来才行,那叫谁扛回去合适呢?而且别人扛回去不一定用得上,说不准还嫌碍事呢。
更要紧的是,人家敢拿回去吗?谁都知道这是谁家的东西,明摆着的事情,能拿回去吗?运动就搞几个月,运动结束以后,都是一个村的,还有几十年,甚至祖祖辈辈要在一起,这个账就算不清了。
所以,除了不知轻重的和工作组硬是要求外,通常是没有去拿的。这毕竟不是斗地主、分田地那回了,四不清干部毕竟不是像地主那样被“扫地出门”、彻底斗垮、甚至连家连人都没有了。连这些农民都知道,四不清干部还会有重新“解放”站起来的日子。
就是这样,分了地主的房,几十年之后,人们还常习惯地说谁家住的是谁谁的房子。这就好理解,为什么土改斗地主时会那么狠,不但是斗得威风扫地,甚至还要从肉体上加以消灭。这样翻身的贫下中农才敢于分他的地、分他的房。因为有了这些地和房,才会拿起枪杆上战场,要去保卫胜利果实。到了“文革”,同样的意思,差不多又演了一遍,一开始就把当权派打翻在地,人们才敢于去造反。
图片
“土改”时,分配实物的照片,地富家的财产都搬出来了。
社教运动还没有到那一步。不敢拿实物,那怎么办呢?就尽量分现金,也好算也好分。要干部尽量退现金。当然那时的村干部哪有这么多现金,实在交实物的,尽量留给队里,另外把实物折合成现金分。
但是现金又从哪儿来呢?村集体又没有那么多。我印象里,为了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分配,好唱完这台戏,我们人大的老师还垫付了些,有好几十呢,比老郭退赔的还要多。这些垫出去的钱,后来是没有下文了。
最后算的结果,每个村民也就是分个三五块钱。分的那天,好象也很平常,乡亲们也没有喜庆的感觉,更没有那种获得第二次翻身的胜利喜悦。无声地排着队,摁下手指印,接过钱便低头数那几张不多的钱。可为了这,费的那些事吧。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,那就是只有“呵呵”了。
图片
组建班子
搞了那么多事,末了,还得把大队、生产队的班子重新搭起来。村里的干部基本恢复原状,真正受到处理的不多,真的心灰意冷不想再干的到是有。
这时候,是反过来,工作组要去求这些基层干部。又是去做工作:要想开一些,这是党对你的一次考验,你的表现还是很好的么,组织上是相信你的,群众还是需要你的,你的前途,我看是大得很唻,这个队,以后就靠你唻。你要是不干,那谁来干啊?叫那个老地主来干?叫那个那个......那个谁谁来干啊?(说个他看不上、相互有矛盾的一个人的名字)最后真的不肯干的也不多。在这个社会里,在台上和台下是不一样的,这一点,大家都明白。
房东老郭还是担任生产队长,兼大队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。他也是不想再干,好在还真是老实本分之人,劝了几句还是接了下来。那贫协的事,从社教结束后,再也没人提起,也没宣布过解散,就那样自生自灭了。
图片
图片
1.群众对干部进行评议,2.四不清干部的档案材料。
运动,看来快要到尾声了。这里想说一点。我在我参加的社教运动的一年中,没看见打过人、死过人。
最主要的原因是,人大师生毕竟是知识分子群体,相对来说,在思想上、行为上杭州在线配资,受暴力倾向、极左观念的影响较小,这类事件发生得也就较少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旺鼎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